
论唐陵与唐文化的主要特点 摘自《乾陵文化研究》
 乾陵博物馆
乾陵博物馆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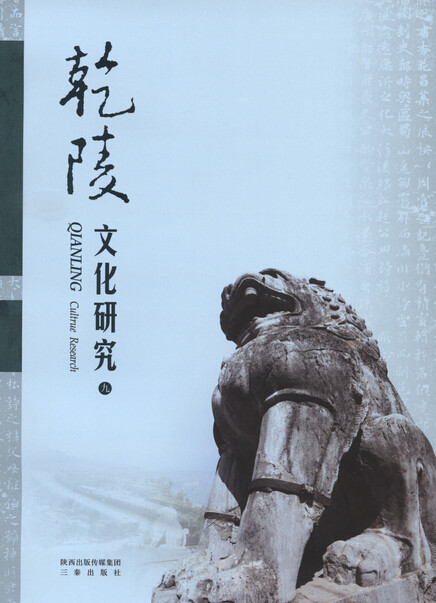
在唐王朝(618-907)存在的289年中,除中宗李显之子少帝李重茂之外,共有21个皇帝(包括女皇武则天)君临天下,其中19个皇帝死后葬在关中,因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一陵,所以关中就出现了18座唐代帝陵,人称“唐代关中十八陵”。唐代帝王为何选择关中渭北一带山峦或塬上为自己的归宿、安息之地?从李渊、李世民父子开始,选择关中为陵地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因为李氏家族自李虎起,“始家长安”[1],其子孙皆为长安人。那为何选中渭河以北地带主要又依山为陵?其一,适宜安葬帝王的骊山脚下北塬已被秦始皇陵所霸占,咸阳塬上又被汉代诸帝陵所据有,因此唐代帝王只好向渭北山峦寻找自己的归宿地。其二,选择渭北山峦营建,可以依山凭险,居高临下,更加宏伟壮观,显示出皇权的高大无比,超越秦汉帝陵的磅礴气势。当然在选择陵地时都要附会“有龙盘凤翔之势”[2],死后能安稳地长眠。其三,防盗。堆土成陵的秦汉帝陵,至唐初几乎全被盗掘,尽人皆知,故贞观九年(635)秘书监虞世南对唐太宗说:“自古及今,未有不亡之国,是无不掘之墓。丧乱以来,汉氏诸陵,无不发掘。”[3]因此,唐代君臣选择陵址时,大讲“薄葬”,“无藏金玉铜铁”[4],透露出营建山陵的主要目的,是为了防止盗掘。
一、关中唐陵的代表
创建贞观之治盛世的唐太宗,晚年患有“气疾”。同许多帝王一样,他幻想长生不老。贞观二十三年(649)五月,他因食金丹中毒使病情加重,己巳(26日)死于终南山翠微宫含风殿,年52岁。八月,葬入昭陵。
唐太宗的昭陵,是他自己选择并在生前营建的。贞观十年(636)十一月,葬已故文德皇后长孙氏于昭陵。这位太宗的贤内助临死前请求“因山而葬,不须起坟,无用棺椁,所须器服,皆以木瓦,俭薄送终”[5]。
昭陵的特点可用几个“最”字来概括:昭陵位于今陕西礼泉县东北20余公里的九山。在18座唐陵中,九山最高,海拔1188米;陵园面积最大,周长60公里;陪葬墓最多,目前已确认有194座,陪葬总人数已远远超过200人[6];在唐代,“因山为陵”最早。“因山而葬”古已有之,如汉文帝刘恒的霸陵,“治霸陵,皆瓦器,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,因其山,不起坟”[7]。至唐代,太宗与文德皇后合葬昭陵。据古代谥法:“圣文周达曰昭。”从此“因山为陵”这种葬制,遂成为唐陵的主要形式。在20座唐陵中占14座。在昭陵众多的石刻艺术品中,以“昭陵六骏”和14尊“诸蕃君长”石雕像为最著名。原来列于昭陵北麓祭坛之内的,有驰名中外的“昭陵六骏”。六骏是6匹曾经伴随李世民东征西讨的骏马。6匹骏马姿态各异,但都矫健雄伟,生气勃勃,是石刻艺术中的瑰宝。“昭陵六骏”采用浮雕法,技术娴熟,造型逼真,充分显示出中国古代雕刻家的卓越才华和精湛技艺。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,致使这六骏石刻也备受欺凌,1914年在被盗过程中遭到破坏。飒露紫、拳毛被盗运到国外,流落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。其余遍体伤痕的四具白蹄乌、青骓(音追,青白杂色的马)、特勤骠、什伐赤今存西安碑林博物馆,用沉默向人们展示着不幸遭遇。在九山北面司马门(玄武门)内原有14尊“诸蕃君长”石雕像,其中有突厥答布可汗阿史那社尔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、高昌王智勇、焉耆王龙突骑支等。标志着唐王朝的疆域辽阔和国力强盛,也象征着天可汗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巨大成功。昭陵是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。雄伟壮丽的仿唐建筑——昭陵博物馆,坐落在李墓的周围。李本名徐懋功,才兼文武、足智多谋、骁勇善战。他原是隋末瓦岗军的主要创建人和将领之一。降唐后屡立战功、出将入相,高宗时是拥护武则天一派官僚的首领。总章二年(669)十二月病死,年76。高宗“为之举哀,辍朝七日”,陪葬昭陵,“所筑坟一准卫(青)、霍(去病)故事,象阴山、铁山及乌德山,以旌破(东)突厥、薛延陀之功”[8]。墓前还依次排列着1对石人,威武庄重;左侧石羊,右侧石虎,各3只。它们又是那样的安详,神态自如,显示出一种自然美与人工美的奇妙结合。特别是墓前矗立着一座高大的《李碑》,又名《李神道碑》,由唐高宗亲自撰文并书丹,足见李在高宗与武则天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文臣武将,是十分珍贵的文物。在昭陵博物馆里陈列的出土文物极其丰富,主要是唐代的墓碑与墓志。昭陵大部分陪葬墓前有碑,几乎每座墓内都有墓志。原有墓碑80多通,现存昭陵博物馆内40多通,墓志20余方。碑刻多为楷书,也有隶、篆、行、草等书体。这些墓志碑刻不仅是唐代书法艺术的精品荟萃,亦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。因此,张沛编著的《昭陵碑石》[9],成为研究唐文化必备的参考书。贞观二十三年(649)五月,太宗死后,22岁的太子李治即位,改明年为永徽元年。在永徽年间(650-655),他勤于政事,任贤纳谏,赏罚分明,处事果断,豁达大度;他继续推行均田制,发展农业生产;他竭力维护国家统一,保持国力强盛。因此史家誉为“永徽之政,百姓阜安,有贞观之遗风”[10]。显庆五年(660)十月以后,高宗因患病委托则天武后处理部分政务,但直到他临死前几个月,他仍然亲自掌管军事、外交大权,亲自裁决宰相任免等国家大事。他并无“昏懦”的表现,其历史功绩是应该肯定的[11]。唐高宗在位34年,则天武后辅政23年。两人之间虽不能说没有一点矛盾,但生活上是情深意笃的伴侣,政治上是志同道合的伙伴,这是从大量史实中归纳出来的结论[12]。武则天一生给唐太宗当了12年才人,后入感业寺当了3年多尼姑;二次进宫后,又当了两年多昭仪、28年皇后、6年皇太后、15年女皇。“在中国古代历史上,还不曾有过另外一个女人,像她那样,经历过那么多的坎坷,遭遇过那么激烈的反对,又享受到那么多的荣耀,拥有那么高的权威”[13]。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、女军事战略家[14]。被誉为盛唐文明的开拓者之一,当之无愧。乾陵位于陕西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,是女皇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合葬陵。弘道元年(683)十二月四日夜,李治崩于洛阳真观殿,遗诏:“七日而殡,皇太子即位于柩前。园陵制度,务从节俭。军国大事有不决者,取天后处分。”[15]遵照高宗的遗言、遗诏,七日后太子李显即位,是为中宗。尊天后武则天为皇太后,并有决定大事权。光宅元年(684)五月,武太后不顾陈子昂等人的反对,命睿宗护送高宗灵柩西返长安。八月十一日,葬高宗于乾陵。其陵位于长安西北,即八卦之乾方,故曰乾陵。《易经》云:“乾,天也。”高宗的尊号“天皇”,故曰乾陵。神龙元年(705)正月,宰相张柬之等发动军事政变,使中宗复位。十一月二十六日,女皇死于洛阳上阳宫,终年82岁。遗制:“庙,归陵,令去帝号,称则天大圣皇后。”[16]神龙二年五月十八日(706年7月2日),中宗遵照“归陵”遗制,不顾严善思等人的反对,葬则天大圣皇后于乾陵。从上述史书记载可以判定,乾陵地宫等主体建筑,是从683年十二月至706年五月完成的。乾陵地面其它建筑及陪葬墓等,是中宗、睿宗执政时期(705年正月至712年七月)完成的。乾陵的营建总费时约28年。其中,从683年十二月至684年八月高宗葬入乾陵,这八个月工程进度最紧张,是由武则天负责策划、审议,指派吏部尚书摄司空韦待价为山陵使,户部郎中、朝散大夫韦泰真为将作大匠,指挥军民10余万人共同完成的。在唐关中十八陵中,乾陵最具有特色:其一,整体气势最宏伟。乾陵建成的初期,可分地面城阙宫殿建筑和地下玄宫建筑。地面宫殿建筑,设置皇城、内城与外城。“规模宏大的乾陵陵园依照京畿长安的布局,其基本结构犹如唐长安城的缩影”[17]。如今乾陵地面建筑虽然早已不复存在,但气势依然宏伟壮观。梁山主峰海拔1047.9米,乾陵玄宫就深凿建于其中;南部二峰东西对峙,俗称“奶头山”。宛若一位睡美人仰天而卧,头枕梁山,脚踏渭北平原。内城南门外司马道东西两侧,是石刻艺术荟萃之地。正如有的专家所说,“经过千百年的风风雨雨,乾陵的地面城阙宫殿已不存在,但相对而言,乾陵是关中十八陵中保护最好的一座,其规模之大,文物之多,景色之美,都是罕见的”[18]。其二,玄宫石门最坚固。《唐会要》记载:“乾陵元宫,其门以石闭塞,其石缝铸铁,以固其中。”[19]《旧唐书》的记载与此相同:“乾陵玄阙,其门以石闭塞,其石缝隙,铸铁以固其中。”[20]1960年参与乾陵隧道发掘的考古专家撰文证实,史书记载可靠,“乾陵筑于石山中,从别的地方打洞进去很不容易,而洞口石条封闭十分牢固,很难开掘。据此,可以断定乾陵不曾被盗过”[21]。其三,帝陵前两座巨碑。乾陵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夫妻皇帝之陵,已经独具特色。陵前又矗立着两座巨大的石碑,更加引人注目。武则天是一位敢想敢干的女强人,光宅元年(684)八月,在高宗入葬乾陵时,她令睿宗李旦在陵前树起早已刻好字的《述圣纪》。此碑文为武则天亲撰,唐中宗李显书写,当在683年十二月至684年二月中宗在位期间所为。此碑位于乾陵陵园朱雀门外司马道西侧。又名《七节碑》,因此碑从上到下用7块巨大石料衔接而成,象征“七曜”,即日、月、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,意喻唐高宗的文治武功犹如“七曜”照耀天下、润泽大地。据说原碑文5100余字,现仅存1630个字[22]。从中可以看出,武则天煞费苦心,竭力讴歌高宗在位34年的文治武功,“谋臣如雨,猛将如云”;而只字不提自己辅政23年的政绩。可以说,此碑文是对唐高宗“昏懦”说的有力驳斥;此座碑,是武则天为铭刻她与唐高宗37年间的真挚爱情而树立的一座永恒的纪念碑。
《无字碑》位于乾陵陵园朱雀门外司马道东侧,因有唐一代未刻一字,故名。《无字碑》是为武则天所立,怀疑者甚少;但何时所立,又为何立碑而不刻一字,迄今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,成为驰名中外的乾陵无字碑之谜。试图解开此谜的说法,包括我的“政局动荡”说,共有9种。今后还会有新说。但我认为,无字碑之谜的存在是件好事。无字碑的存在,使梁山更显高大;无字碑的存在,使乾陵更加宏伟;无字碑的存在,使武则天更具有魅力。武则天千古,无字碑永存[23]。
唐代皇帝陵,除关中十八陵之外,昭宗的和陵位于河南偃师,哀帝的温陵位于山东菏泽。唐朝末代两座孤独的唐陵,成为历史对亡国之君的嘲弄。关中十八陵中,只有昭陵、乾陵两座,1961年3月4日,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此外还有一座唐陵,它不是皇帝陵,而是“号墓为陵”,也被列入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就是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的顺陵。因此特别引人注目。
二、乾陵文化的主要内涵
唐陵文化是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乾陵是“唐陵之最”,唐文化内涵最为丰富:其一,乾陵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。其二,“乾陵以山为阙,气势雄伟,规模宏大,陵园周围40公里,实为唐代皇陵之最”[24]。其三,在唐十八陵各博物馆、文管所中,唯有乾陵博物馆从2005年起创办专刊《乾陵文化研究》,每年出版一期,向海内外公开发行。现已出版9期,影响广泛。
1 . 高宗、武则天时代的盛唐文化
唐陵文化,首先应包括每座唐陵陵主人所处时代的文化。高宗、武则天时代的盛唐文化,辉煌灿烂,我已有两篇专文论述[25]。仅就科举来说,高宗创建了制举,发展了科举制;武则天创立殿试和武举,使科举制度更加蓬勃发展。高宗时期(649-683)中进士者555人,武则天独掌政权时期(684-705)中进士者464人。高、武时期共有1019人中进士。这具有划时代意义,其前官僚队伍的成员主要由门阀士族及其子弟组成;其后,则主要由进士出身的学人任官僚、执掌相权。进而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。
2 . 乾陵的建筑艺术
唐陵建筑是唐文化的组成部分,更是陵墓文化的重要内容。诚如文物专家所言,“唐陵分为两种形式:一种是建于高原的覆斗形土冢,包括献(李渊)、庄(李湛)、端(李炎)、靖(李儇)四陵;另一种是利用山川的自然形式,在山南面开凿墓室而成陵,其余十四陵墓均属此类”[26]。乾陵整个建筑布局,充分展现了“因山为陵”的模式。它利用梁山主峰(海拔1047.9米)和南面的两个东西对峙的小峰,作为布局的骨架,确实宛如一位巨美人仰面躺在那里。据文物专家根据有关资料推断,乾陵陵园内的建筑仿照唐长安城格局营造。这个推断是可信的。迄今地面宫殿建筑群虽早已不复存在,但考古工作者中的画家、制图师,依据懿德太子墓壁画《阙楼图》、文献记载、实地勘查再加以想像而绘制出来的乾陵古建筑复原图,还是那么宏伟壮观,令人痴迷。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,乾陵建筑艺术是值得深入研究的。
3 . 17座陪葬墓
乾陵的陪葬墓,分布在梁山山麓东南一带。史书记载有16座:章怀太子李贤、懿德太子李重润、泽王李上金、许王李素节、王李守礼、义阳公主、新都公主、永泰公主、安兴公主、特进王及善、中书令薛元超、特进刘审礼、礼部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、右仆射刘仁轨、左卫将军李谨行、左武卫将军高侃等[27]。另一座是尚书右仆射杨再思墓。史载,杨再思于景龙三年(709)病故,“赠特进、并州大都督,陪葬乾陵,谥曰恭”[28]。这17座陪葬墓,是乾陵文化的17个闪光点。从1960年8月开始,文物部门先后发掘了永泰公主墓、懿德太子墓、章怀太子墓及李谨行墓、薛元超墓,特别是前三墓,出土文物之多,壁画之精美,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。从此乾陵扬名海内外。自2005年《乾陵文化研究》创刊以来,新一轮研究乾陵文化热潮掀起,不仅探讨乾陵陪葬墓墓主人的论文不断问世,其专著继《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》(拜根兴、樊英峰著)之后,《懿德太子与懿德太子墓》(樊英峰、拜根兴著)、《章怀太子与章怀太子墓》(樊英峰、洪海安著)等著作,亦将陆续出版。
4 . 乾陵的石刻艺术
据有人统计,“唐代关中十八陵,原有石刻(不包括陪葬墓)共1084件,现在包括残件在内仅存496件”[29]。其中现存石刻件数最多的当属乾陵。乾陵石刻较为集中地分布在陵园朱雀门外,玄武、青龙、白虎三门较少。内城四门各有1对石狮,北门立6匹马(今存1对)。其余均集中排列在梁山主峰之南坡、南司马道第二、三道门之间,分东西两排。计有1对石狮;石狮之南有61尊蕃臣像(东群29件、西群32件);朱雀门西阙楼之前的述圣纪碑,朱雀门东阙楼前的无字碑;两碑之南有10对石人像(亦称翁仲);石人像之南有仗马和马夫5对;仗马之南有鸵鸟1对;鸵鸟之南有翼马1对;翼马之南,第二道门内有高大的华表1对。堪称“唐代石刻艺术露天博物馆”。
这些盛唐石刻艺术的精品,不仅吸引众多游人的眼球,而且招徕许多专家学者的倾心研究、热烈争论。例如鸵鸟,原产于非洲,后由波斯(今伊朗)传入中国。“所以,石刻鸵鸟是一千多年前,唐朝同非洲人民友好往来的物证”[30]。近年来有文物专家提出“乾陵神道鸵鸟为射侯”说,他认为“乾陵神道石鸵鸟形制与古射中所记之射侯非常相像”,“所以,石鸵鸟应当是仿古射侯而设”[31]。此说发表不久,另一位考古专家便撰文反驳,认为“唐代,谒陵,不需要经过射礼的遴选”,“石鸵鸟与射侯是两码事”,并问“鸵鸟若为射侯,侯道设在何处?”[32]
再譬如,关于乾陵61尊石人像的讨论。这61尊石人是何身份?上世纪80年代以前,较普遍的看法是,这是为参加高宗葬礼的61位宾王刻石立像,所以叫“六十一宾王像”。但到上世纪80年代初,有专家经过考释,认为这是为参加高宗葬礼的国内各少数民族酋长、当时唐朝各级官员刻石立像,不应称为“宾王”,而应称为“蕃臣”,并确认36尊石人像是国内原少数民族酋长即诸蕃君长[33]。此说后来较为普遍流行,至1995年乾陵“六十一宾王像”说明牌遂被“六十一蕃臣像”说明牌所取代。但人们要问:确认36尊石人像为国内诸蕃君长,那另外25尊石像又是何身份?其定位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曾在韩国攻读博士学位,如今为陕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、博导的拜根兴,对唐朝与新罗的关系史颇有研究,著述甚多。他经过实地考察和研究,断定乾陵六十一蕃臣像东群东南角的一尊石像为新罗使者。此说得到韩国专家的认可[34]。另外,61尊石人中仅有两尊人头残存,其余皆无头,是何原因?有学者认为,主要原因是毁于明世宗嘉靖年间(1522-1566)的关中大地震[35]。此外还有“原竖64尊,现在60尊(误为61尊)说”[36],都值得进一步揭谜,使石刻艺术的研究更加光彩夺目。
5 . 唐墓壁画、线刻画在乾陵17座陪葬墓中,规格最高的当属“号墓为陵”的永泰公主墓、懿德太子墓以及章怀太子墓。三墓中出土的100多幅壁画,题材广泛,制作精美,绚丽多姿,人物逼真,形态各异,反映了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,幅幅堪称无价之宝,在乾陵文化中,是迄今最辉煌灿烂的部分。如章怀太子墓中的《打马球图》《狩猎出行图》《观鸟捕蝉图》《礼宾图》(亦称《客使图》),永泰公主墓中的《宫女图》(亦称《仕女图》),懿德太子墓中的《阙楼图》《车马图》《驯猎狗图》等等。内容极其丰富,是研究唐代前期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建筑、文化状况、各民族关系、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资料。“乾陵石线刻画是指以刀代笔,以石为纸,利用白描形式而雕刻出的一种艺术作品,它是隋唐陵墓石刻艺术中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”[37]。著名的线刻画有永泰公主墓石椁线刻画——赏花嬉鸟图等。
6 . 乾陵唐三彩
唐三彩是唐代铅釉陶质生活用品和捏塑艺术用品的总称。“三彩”是多彩的意思,并非指三种色彩。釉的颜色有黄、绿、白或黄、绿、赭等,交错使用。唐三彩是我国彩陶艺术史上的奇迹,色泽绚丽夺目,造型逼真生动。其中以上述三座陪葬墓出土的三彩俑、三彩马最著名,数量亦最多,多为随葬用品。有专家统计:永泰公主墓出土81件,章怀太子墓出土262件,懿德太子墓出土143件[38]。
乾陵文化的特征及学术价值,是唐陵的典型代表,是盛唐文化的辉煌体现。它生动地反映了唐朝各民族的友好关系,亦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。
三、唐文化的主要特点
唐陵文物的丰富遗存,与史书文献记载的唐文化,相互印证,相互补充,更能彰显出唐文化的历史悠久,博大精深,影响广泛。
1 . 继往开来,南北交融
众所周知,秦汉以前的古代文化,带有明显的地域性。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,特别是汉武帝使国家强盛并派了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以后,逐渐形成融合各民族文化于一体的中华文化。但自西晋灭亡至隋灭陈之前(317-589),长达270年的南北分裂,又造成传统文化的重新分裂。而隋的统一又很短暂(589-618),实际不足30年。因此至唐初人们还能感受到南北文化的裂痕。有人认为唐文化主要来源于南方宋齐梁陈文化,这一看法不够全面。实际上,唐文化既来自其前的南方,亦继承了北方文化的优秀传统。例如唐初行之有效的均田制,便是来自北魏孝文帝的改革;导致大唐前期国力强盛的府兵制,来源于西魏宇文泰的创造。这是古代鲜卑族对中华民族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。又例如,唐初史家李大师不满意“南书谓北为‘索虏’,北书指南为‘岛夷’”[39]的地域偏见,开撰南北文化融合的史书;其子李延寿继承父志,撰成《南史》《北史》,纠正了以往修史的地域偏见。再譬如,唐太宗在以儒学治国的过程中发现,长期国家分裂已造成南、北儒学的很大差异,各有不同的版本和注疏。于是他先命颜师古等人统一《五经》(《周易》《尚书》《毛诗》《左传》《礼记》)。贞观七年(633)完成并颁行天下;其后,他又命孔颖达等人统一《五经》注疏。至永徽四年(653)三月,高宗“颁孔颖达《五经正义》于天下,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”[40]。由此可见,国家的统一,对于文化的发达至关重要。
2 . 胡汉结合,异彩纷呈
由于唐朝前期的皇帝具有鲜卑族的血统,唐太宗被各民族尊为“天可汗”,推行各民族较为平等的民族政策,以下诸帝包括女皇武则天都继续推行各族文化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,使唐文化具有十分明显的胡化倾向[41]。主要表现为:婚姻礼俗受鲜卑、突厥等族的影响,妇女贞节观念极其淡薄,改嫁成风;喜欢吃胡饼,穿胡服、戴胡帽,我们从昭陵、乾陵陪葬墓壁画中,可以看到其绚烂的风姿;乐舞充满胡音、胡调、胡姿。西域三大乐舞(胡旋、胡腾、柘枝)在长安、洛阳等地盛行[42]。杨贵妃擅长胡旋舞,并主演《霓裳羽衣舞》。胡人安禄山为取媚唐玄宗,晚年“腹垂过滕,重三百三十斤”,但“作胡旋舞,疾如风焉”[43]。与此同时,入居内地的胡人,读《五经》,学儒学,逐渐汉化。这种胡汉结合、交融,使大唐文化绚烂多姿,异彩纷呈,充满生机,更具有魅力。
3 . 三教鼎盛,共同发展
传统儒学创始于孔子、孟子,故又称孔孟之道,发展至隋唐之际,与道、佛二教并称“三教”。道教创始于东汉中后期,追尊春秋后期的老子为创始人。佛教创始于古印度,因其始祖为释迦牟尼,故又称释教,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内地之后,经东汉、魏晋南北朝、隋,至唐初有很大发展,形成各大宗派,并逐渐中国化。
唐朝21帝中,除后期唐武宗重道灭佛之外,都不同程度地尊儒信道崇佛,只是各个时期各有侧重。特别是前期几位皇帝,竭力推行三教兼容、共同发展的宗教政策。唐高祖李渊尊儒,“颇好儒臣”[44]。太宗更喜欢儒术,说他与儒学的关系,就像鱼与水、鸟和翼的关系,“失之必死,不可暂无”[45],尊孔子为“先圣”。高宗还亲临山东曲阜,“幸孔子庙,追赠太师”[46]。武则天当上女皇后,以自撰的《臣轨》为治国纲领[47]。而《臣轨》的中心思想,是儒家的“臣事君以忠”。唐高祖信道,自称自己是道教始祖李聃的后代,下令道教为三教之首。太宗亦多次讲自己是老子的后代,规定道士、女冠在僧尼之前。高宗追封老子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。武则天以道教为养生之术,遣道士胡超于嵩山上放置“除罪金简”,“乞三官九府,除武罪名”。高祖、太宗虽不痴迷佛教,但亦不打压佛教。太宗对玄奘法师非常敬重。高宗、武则天都崇佛,乾封元年(666)正月登泰山封禅之前,二人在灵岩寺住了七八天[48]。武则天不仅信佛,还利用佛教《大云经》为当女皇制造舆论。唐代前期诸帝的尊儒信道崇佛,促使三教鼎盛,共同发展,因而带动了科举、书法、乐舞、建筑、文学艺术、历史学等各个文化领域的绚丽多姿,争奇斗妍。
4 . 博大精深,影响久远
博大,就是广博宏大,包括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;精深,就是各个文化领域里都有杰出代表,都有传世精品。如大佛学家、翻译家、旅行家玄奘法师,大军事家李靖、李,大书法家欧阳询、颜真卿、柳公权、怀素、张旭,大画家阎立本、吴道子,大诗人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王维、杜牧,大散文家韩愈、柳宗元等等,不胜枚举。在史学方面,有唐朝前期完成的《晋书》《梁书》《陈书》《北齐书》《周书》《隋书》和《南史》《北史》,在正史《二十四史》中占了8部,人称“唐八史”[ 4 9 ]。另外还有《史通》《大唐六典》《通典》等著作。《唐律疏议》被称为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,世界法系之中华法系的代表作。
唐文化对其后五代十国、宋辽夏金元明清的文化都有重要影响。迄今仍为广大群众所喜爱,其中的传世佳作,皆为祖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。唐代的传世文物,如昭陵六陵、乾陵壁画、大小雁塔、大明宫遗址,等等,皆令游人流恋忘返,称赞不已。唐文化对世界各国,特别是东方诸国,都产生过巨大影响。唐“贞观之治”传入日本,引发孝德天皇从大化元年(654)开始的“大化革新”。在日本入唐僧中,吉备真备和空海回国后,利用汉字楷书偏旁及草书创造了日本文字片假名和平假名。唐朝名僧鉴真东渡日本,在日本广泛传播唐文化。唐文化不仅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国宝,而且迄今仍然具有东方文化的魅力,形成世界公认的环太平洋的“唐文化圈”,应属于世界文化遗产。
[1]《资治通鉴》卷185高祖武德元年条,中华书局,1956年,第5771页。
[2](宋)王溥:《唐会要》卷20《陵议》,中华书局,1955年,第397页。
[3] [4]《唐会要》卷20《陵议》,第393页。
[5]《旧唐书》卷51《文德皇后传》,中华书局,1975年,第2166页。
[6]参刘向阳:《唐代帝王陵墓》,三秦出版社,2003年,第56页。
[7]《汉书》卷4《文帝纪·赞曰》,中华书局,1962年,第134页。
[8]《旧唐书》卷67《李传》,第2488页。
[9]张沛:《昭陵碑石》,三秦出版社,1993年。
[10]《资治通鉴》卷199高宗永徽元年条,第6270-6271页。
[11]详见拙作《唐高宗“昏懦”说质疑》,刊《人文杂志》1986年第1期。
[12]见拙作《唐高宗研究的几个问题》,载《乾陵文化研究》(三),三秦出版社,2007年。
[13]赵文润、王双怀:《武则天评传》(2版),三秦出版社,2000年,第7页。
[14]详见拙著《武则天》,西安出版社,2007年,第229-261页。
[15]《旧唐书》卷5《高宗本纪》,第112页。
[16]《旧唐书》卷6《则天皇后本纪》,第132页。
[17]樊英峰、雒长安、张永祥:《乾陵》,陕西旅游出版社,1999年,第3页。
[18]王双怀:《荒冢残阳——唐代帝陵研究》,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,2000年,第59页。
[19]《唐会要》卷20《陵议》,第396页。
[20]《旧唐书》卷191《严善思传》,第5102页。
[21] [40]杨正兴:《乾陵》,载《武则天与乾陵》,三秦出版社,1986年。
[22]樊英峰:《武则天与乾陵〈述圣纪碑〉》,载《武则天研究论文集》,山西古籍出版社,1998年。
[23]详见拙作《论乾陵无字碑之谜》,原载《乾陵文化研究》(二),三秦出版社,2006年。后收入拙著《武则天与唐高宗新探》,三秦出版社,2008年。
[24]陈安利:《唐十八陵》,中国青年出版社,2001年,第50页。
[25]详见拙作《论唐高宗在文化史上的贡献》,载《人文杂志》1997年第2期;拙作《论武则天在文化史上的贡献》,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《中华传统文化与新世纪》,三秦出版社,2004年。
[26]《唐十八陵》,第24页。
[27]《唐会要》卷21《陪陵名位》,第414页。
[28]《旧唐书》卷90《杨再思传》,第2919页。
[29]《唐十八陵》,第184页。
[30]《唐代帝王陵墓》,第99页。
[31]秦建明:《乾陵神道鸵鸟为射侯说》,《文博》2006年第3期。
[32]韩伟:《〈乾陵神道鸵鸟为射侯说〉驳正》,载《乾陵文化研究》(三),三秦出版社,2007年。
[33]陈国灿:《唐乾陵石像及其衔名研究》,《文物集刊》1980年第2期。
[34]拜根兴:《唐朝与新罗往来研究二题——以西安周边所在的石刻碑志为中心》,《当代韩国》2011年第3期。
[35]王晓莉:《乾陵61尊石人像有关问题再探讨》,载《武则天与嵩山》,中华书局,2003年。
[36]《唐代帝王陵墓》,第106页。
[37]樊英峰:《关于乾陵文化的再探讨》,载《武则天与咸阳》,三秦出版社,2001年。
[38]《唐十八陵》,第359页。
[39]《北史》卷100《序传》,中华书局,1974年,第3343页。
[40]《旧唐书》卷4《高宗本纪》,第71页。
[41]详见拙作《论唐文化的胡化倾向》,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》1994年4期。
[42]详见拙作《隋唐时代的西域三大乐舞》,台湾《历史月报》1997年第1期。
[43]《旧唐书》卷200《安禄山传》,第5368页。
[44]《旧唐书》卷189《儒学传序》,第4940页。
[45](唐)吴兢:《贞观政要》卷6。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年,第195页。《资治通鉴》卷192太宗贞观二年条,第6054页。所载与此略同。
[46]《旧唐书》卷5《高宗本纪》,第90页。
[47]《资治通鉴》卷205则天后长寿二年条,第6490页。
[48]《资治通鉴》卷201高宗麟德二年——乾封元年,第6346页。
[49]参阅赵文润主编《隋唐文化史》第九章第四节《唐代八史》,第345-350页;牛致功撰该书《绪论》,第1-20页,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2年。
(赵文润,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,教授)



